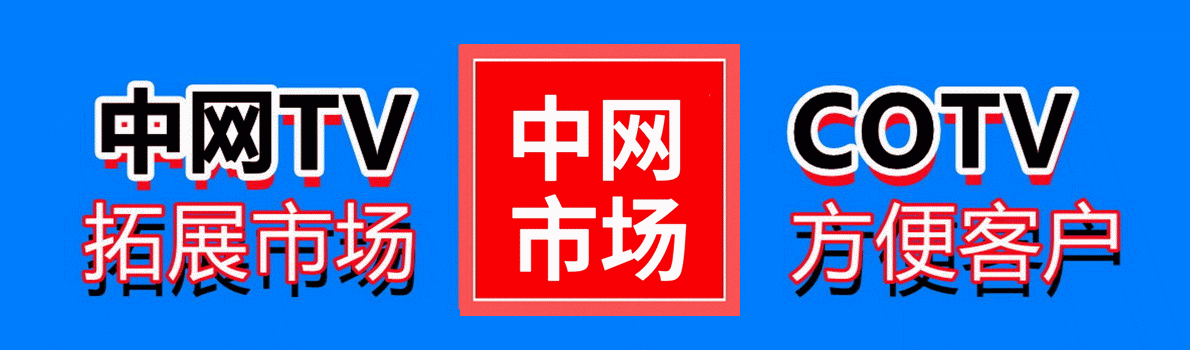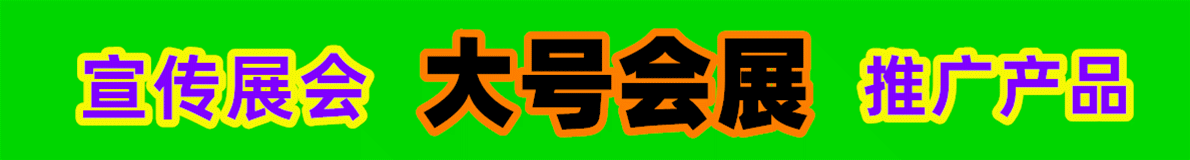央行貨幣政策司姚余棟撰文認(rèn)為降低政府杠桿率是個(gè)全球性難題,凱恩斯主義刺激政策存在極限,政府資產(chǎn)負(fù)債表在企業(yè)和家庭部門完成去杠桿化進(jìn)程后才能恢復(fù),他認(rèn)為應(yīng)轉(zhuǎn)向供給方面的改革創(chuàng)新,在保持較快增長中逐步去杠桿。
以下是姚的全文:
上世紀(jì)70年代最重要的流行單詞是“極限”這個(gè)詞。也許沒有任何一本書比羅馬俱樂部的報(bào)告更好地切中上世紀(jì)70年代氣氛的要害,給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,報(bào)告的題目是:《增長的極限》。可惜,人們當(dāng)時(shí)錯(cuò)誤地判斷了極限。實(shí)際上,“極限”不在經(jīng)濟(jì)增長,而在于當(dāng)時(shí)的流行性經(jīng)濟(jì)政策。在21世紀(jì)的前20年里,人類正走向一些它在上個(gè)世紀(jì)沒有認(rèn)識、也不想認(rèn)識的極限,但現(xiàn)在必須認(rèn)識的,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的極限。
凱恩斯在1936年發(fā)表《就業(yè)、利息與貨幣通論》這一著作,成為20世紀(jì)最偉大的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著作之一;《就業(yè)、利息和貨幣通論》的思想也依然在深深地影響著今天全球的經(jīng)濟(jì)政策和經(jīng)濟(jì)實(shí)踐。
政府財(cái)政政策在凱恩斯主義問世前,各國基本上奉行“量入為出,略有盈余”的原則。凱恩斯主義打破了這一傳統(tǒng),側(cè)重宏觀需求端的管理,主張通過調(diào)節(jié)貨幣和財(cái)政政策調(diào)控總需求,提高社會(huì)的有效需求水平,從而有助于實(shí)現(xiàn)充分就業(yè)。
20世紀(jì)30年代大蕭條之后世界各國依賴凱恩斯的擴(kuò)張政策,在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爆發(fā)后徹底走出大蕭條的陰影,奠定了凱恩斯主義在過去80年歷史當(dāng)中不可動(dòng)搖的地位,雖然歷經(jīng)國際金融危機(jī),全球經(jīng)濟(jì)依然享受著凱恩斯式調(diào)控帶來的信用繁榮。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(jī)之后,凱恩斯主義并未終結(jié)。“只要這個(gè)世界有需要,凱恩斯的思想就會(huì)一直存在下去。”
凱恩斯在第一章何謂《通論》中寫道,“我把本書命名為就業(yè)、利息和貨幣通論,用以強(qiáng)調(diào)前綴‘通’字。”。但是,筆者指出,凱恩斯的“通論”不是他本人設(shè)想的“通論”,僅僅是一個(gè)部分均衡模型,沒有包括經(jīng)濟(jì)特別是政府部門的資產(chǎn)負(fù)債表,存在的致命疏漏就是忽略了政府部門資產(chǎn)負(fù)債表。財(cái)政政策主要影響政府資產(chǎn)負(fù)債表。凱恩斯主義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蘊(yùn)含著這樣一條假設(shè):有杠桿就有增長,沒有杠桿就沒有增長。政府資產(chǎn)負(fù)債表杠桿率上升到一定程度,會(huì)不可避免地產(chǎn)生兩個(gè)效應(yīng):
一是債務(wù)陷阱。財(cái)政上經(jīng)年累月地入不敷出,只靠借債彌補(bǔ)赤字,赤字政策常規(guī)化,政府負(fù)債越來越重。政府杠桿率上升到一定程度,利率上升,會(huì)出現(xiàn)債務(wù)陷阱,類似人體“糖尿病”的綜合并發(fā)癥,往往不可逆。2013年國際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界最有戲劇性的事件,莫過于圍繞著名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卡門·萊因哈特和肯尼斯·羅格夫2010年前在《美國經(jīng)濟(jì)評論》上發(fā)表的一篇論文的爭論。卡門·萊因哈特和肯尼思·羅格夫2010年利用44個(gè)國家時(shí)間跨度達(dá)200年的大樣本數(shù)據(jù)分析了增長與政府債務(wù)規(guī)模的關(guān)系,結(jié)果表明當(dāng)政府債務(wù)占比GDP高于90%時(shí),長期增長率的中位數(shù)將下降一個(gè)百分點(diǎn),平均增長率下降更為顯著。這篇文章為歐債危機(jī)爆發(fā)后IMF與德法等國要求南歐國家實(shí)施財(cái)政緊縮政策的做法奠定了理論基礎(chǔ)。而到2012年年初,幾位美國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發(fā)現(xiàn),萊因哈特與羅格夫的論文在數(shù)據(jù)計(jì)算過程中存在操作失誤,在樣本選擇過程中存在主觀偏差,其加權(quán)方法也令人質(zhì)疑。但無論如何,過高的政府債務(wù)對經(jīng)濟(jì)增長帶有嚴(yán)重危害性是傳統(tǒng)智慧。
二是“明斯基時(shí)刻”,即自我實(shí)現(xiàn)的政府債務(wù)危機(jī)。明斯基的觀點(diǎn)主要在金融市場,提出了金融不安定假說。筆者把它應(yīng)用于政府債務(wù):好日子的時(shí)候,政府敢于財(cái)政刺激;好日子的時(shí)間越長,政府冒險(xiǎn)越多,直到過度冒險(xiǎn)。一步一步地,政府債務(wù)會(huì)達(dá)到一個(gè)臨界點(diǎn),其資產(chǎn)所產(chǎn)生的現(xiàn)金不再足以償付他們用來獲得資產(chǎn)所舉的債務(wù)。投機(jī)性資產(chǎn)的損失促使政府債券投資者收回其貸款。國際金融危機(jī)后的一個(gè)基本共識就是人類無法準(zhǔn)確確定資產(chǎn)價(jià)格,就是實(shí)際利率是多均衡的,不是唯一均衡的。歐債危機(jī)是最好的例子。希臘債務(wù)危機(jī)當(dāng)中,每個(gè)投資者都會(huì)擔(dān)心希臘“破產(chǎn)”,從而拋售希臘國債或者拒絕購買新的希臘國債,以規(guī)避可能的損失,這會(huì)導(dǎo)致利率大幅度飆升,希臘國債價(jià)格急劇下跌,收益率大幅攀升,最終導(dǎo)致希臘融資成本劇增,無法發(fā)行新的國債,希臘反而更加快速地接近“破產(chǎn)”邊緣。
全球政府債務(wù)已經(jīng)遠(yuǎn)遠(yuǎn)超過1936年《通論》發(fā)表時(shí)的水平,達(dá)到一個(gè)令人擔(dān)憂的程度,財(cái)政空間已經(jīng)越來越小。IMF數(shù)據(jù)庫沒有直接提供全球債務(wù)的整體數(shù)據(jù),有學(xué)者利用國別數(shù)據(jù)進(jìn)行了大量計(jì)算,結(jié)果顯示:從規(guī)模看,2014年,全球債務(wù)總量預(yù)估值為61萬億美元左右,自2002年以來連續(xù)13年同比上升,并首次超過60萬億美元大關(guān)。根據(jù)IMF的預(yù)估數(shù)據(jù),2014年發(fā)達(dá)經(jīng)濟(jì)體的總債務(wù)為51萬億美元左右;發(fā)達(dá)經(jīng)濟(jì)體總債務(wù)占全球總債務(wù)的比例為83.5%;發(fā)達(dá)經(jīng)濟(jì)體的負(fù)債率為108%,超出100%的技術(shù)破產(chǎn)線。2014年,新興市場體的總債務(wù)為10.07萬億美元,負(fù)債率則為34%左右。從分布來看,債務(wù)過高的風(fēng)險(xiǎn)主要集中在發(fā)達(dá)經(jīng)濟(jì)體,這非常不利于債務(wù)重組。
亞當(dāng)·斯密早在1776年《國富論》中就有關(guān)于“國家破產(chǎn)”制度的設(shè)想:“當(dāng)國債積累到一定程度,我相信,就不會(huì)有完全償清的時(shí)刻。如果說利用國家收入解脫國債的事例曾經(jīng)有過,那也總是通過破產(chǎn)解除的。當(dāng)一個(gè)國家需要宣布破產(chǎn)時(shí),就如同一個(gè)個(gè)人需要宣布破產(chǎn)時(shí)一樣,一個(gè)公平、光明正大和公開承認(rèn)的破產(chǎn)不論對債務(wù)人的名譽(yù)和對債權(quán)人的利益都將是一個(gè)損失最小的措施。”但政府債務(wù)重組缺乏國際機(jī)制。2001年,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副總裁安妮克魯格(Anne Kruger)嘗試了主權(quán)債務(wù)重組機(jī)制,可惜沒有成功。政府債務(wù)的“明斯基時(shí)刻”一旦來臨,很可能導(dǎo)致零利率,經(jīng)濟(jì)陷入流動(dòng)性陷阱的“黑洞”。中央銀行不得已背水一戰(zhàn),實(shí)施大規(guī)模量化寬松(QE)。但能否把經(jīng)濟(jì)拉出流動(dòng)陷阱,還不得而知。當(dāng)前日本和歐洲就面臨這個(gè)困境。
降低政府杠桿率是個(gè)全球性難題,“去杠桿化”的漫長過程,對經(jīng)濟(jì)增長確實(shí)構(gòu)成了挑戰(zhàn)。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“債務(wù)與去杠桿化:全球信貸泡沫及其經(jīng)濟(jì)后果”認(rèn)為,去杠桿有四種途徑:緊縮政策,高通貨膨脹,拖延債務(wù)和增長(經(jīng)濟(jì)增長速度高于債務(wù)增長速度)。該報(bào)告認(rèn)為,政府部門去杠桿往往在企業(yè)部門去杠桿之后。筆者認(rèn)為,政府資產(chǎn)負(fù)債表存在野村證券辜朝明提出資產(chǎn)負(fù)債表衰退,對應(yīng)著凱恩斯主義的極限,也就是在企業(yè)和家庭部門完成去杠桿化進(jìn)程后才能恢復(fù)。
既然去杠桿如此艱難,那么最好的藥方是預(yù)防政府杠桿率過高,不能過度使用凱恩斯主義刺激政策。凱恩斯主義存在極限,也就是說,政府債務(wù)杠桿率必須低于某一個(gè)“紅線”,必須將凱恩斯主義“關(guān)進(jìn)籠子”。凱恩斯在《和約的經(jīng)濟(jì)后果》中充滿憂郁地質(zhì)問,“人類還能夠忍受多少,或者人類從哪個(gè)方向上能夠?qū)ふ业矫撾x災(zāi)難的方法,又有誰能夠說出呢?”
治療糖尿病的幾乎唯一方式是防止糖尿病。中國新供給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研究群體提出了“中醫(yī)”和“西醫(yī)”的比喻。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可比喻為“西醫(yī)”,而新供給所強(qiáng)調(diào)的供給管理更像是“中醫(yī)”。 “西醫(yī)” 沒有也不應(yīng)該消亡,而應(yīng)長期有限合理使用,其療法往往可救急,但副作用也大。中醫(yī)療法如文火慢煮,綜合施治,容易把握火候,引出的結(jié)果會(huì)味道濃厚。在供給端改革是各國包括發(fā)達(dá)國家的紅利來源,“中醫(yī)”療法的余地依然很大。應(yīng)從之前國際主流的需求管理“西醫(yī)”方式,更自覺、更積極地轉(zhuǎn)向供給方面的改革創(chuàng)新,防止對“西醫(yī)”過度依賴,在保持較快增長中逐步去杠桿,采用“中醫(yī)為主、西醫(yī)配合”的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合理結(jié)合的綜合療法。但在經(jīng)濟(jì)嚴(yán)重下滑和金融出現(xiàn)系統(tǒng)風(fēng)險(xiǎn)時(shí),或當(dāng)經(jīng)濟(jì)跌入流動(dòng)性陷阱中時(shí),仍應(yīng)果斷使用“西醫(yī)”療法。
來源: 最新紡織